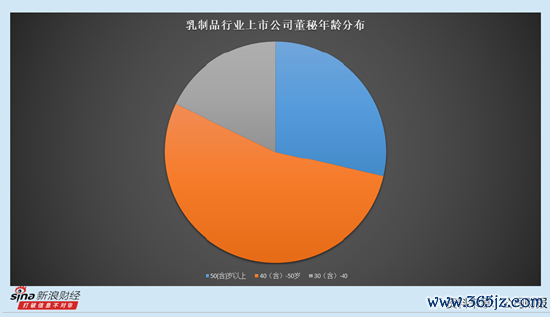一
说到海鲜,敝乡东说念主总难免有几分自诩。中国大陆海岸线最长的十大城市里,我老家台州稳居老七。各地皆有《摇啊摇,摇到外婆桥》的儿歌,到了我老家,便成了海鲜版——“摇、摇、摇,摇到外婆桥;白米饭,鲞汤浇,黄鲫鲓,箸样长;饭呒熟,再摇摇”,是带着一片童确切鲜好意思。
海鲜是老家东说念主的通关密码。儿歌中的黄鱼鲞冬瓜汤浇白米饭,我从小吃到大。在敝乡,海鲜不错单独称霸,也不错与米饭、面条、年糕等碳水结成搭子,并不违和粗俗。
带鱼饭是敝乡最常见的海鲜饭。作念好一碗带鱼饭,先要有条好带鱼。好带鱼的选好意思表率是“三小一厚”——个小、头小、眼小、肉膛厚。“小眼带鱼”比“大眼带鱼”滋味好得多。冬至前后的“雷达网”油带,则是膏腴巅峰。
小眼带鱼清蒸、红烧、煮萝卜丝,皆很可口。渔民出海,会在船上作念带鱼饭,带鱼内脏惩办干净,用海水囫囵一冲,整条带鱼“哐当”丢进锅里,与米饭同煮。饭熟鱼香,拎起带鱼一抖,白茫茫的嫩肉雪片似的掉进锅里,用筷子略加搅动,关盖焖熟,鲜好意思的带鱼饭就出炉了。肥厚嫩糯的油带,自带油脂,与米饭一交融,满锅的鲜味,莫得半点腥膻之气。
二
早年常去三门,辉煌赶赴吃河豚,秋分后去吃青蟹。当地的青蟹饭,以陈大哥酒浸醉青蟹,蟹脐塞上姜丝去腥,整只蒸熟,蟹汁、膏黄渗进米饭,真鲜!也有蟹黄饭,带膏的白蟹或青蟹蒸熟,剔出蟹肉、蟹膏,径直拌进米饭,是扑鼻的鲜香。
有一年到温岭渔村采风,在村尾一家不起眼的小饭铺里,吃过墨鱼饭。刚出水的大墨鱼,掏净肚肠,浸泡好的白胖糯米塞进墨鱼肚,隔水蒸熟。外圈墨鱼内圈米饭,相当有嚼头,有点访佛江南的桂花糯米莲藕,但鲜味胜过百倍。
蔡澜写过鱿鱼饭,渔东说念主把小小的活鱿鱼扔进酱油里,鱿鱼大口吞食酱油,身子带着咸味。烧饭时,把活鱿鱼径直铺在饭上,熟后,鲜好意思得能连吃三碗。缺憾,我没吃过。
龙虾泡饭和鱼翅捞饭最早出目下粤闽,这股风几十年前就吹进浙东。饭局尾声,总要来份龙虾泡饭抛弃。可口的龙虾泡饭,要用虾头虾壳提前熬煮高汤,再加入小数奶油、椰浆调味,龙虾肉质紧实鲜活,汤汁招揽了海鲜的清甜,隔夜的米饭粒粒紧实,吸满汤汁后软糯入味。鱼翅泡饭更高档一些,用老鸡、老鸭、火腿、筒骨、干贝等原料慢火熬成鲍汁,勾芡后,浓稠鲜好意思,鱼翅爽滑,拌上白米饭,每粒米皆裹满鲜味。粤闽菜系,矜重六朝韵文般的铺陈,台州菜与之比,显得直白通透,顺心感扫数。
客岁去上海,在外滩的林家一饭店吃过一说念东海大黄鱼焖饭。主办东说念主林好意思均是台州东说念主,长得我见犹怜,笑起来腮帮子会抖,开店选址有海边东说念主耕海烹鲜的大气,初到上海,竟敢直愣愣选在寸土寸金的外滩边上。他从小在海边长大,见过多样风波,吃过多样海味,当地渔民把刚打捞上的渔获,放在土灶上与大米焖煮,扑鼻鲜香。到了他这里,就改造成了黄鱼焖土灶饭。野生黄鱼切块,以家烧的面貌入味,与晚稻米一说念,在土灶中焖熟,吃时再浇入浓香黄鱼汤。锅底带焦香的米饭,喷香酥脆,咬起来“咯吱”有声。
几十年前的野生黄鱼是白菜价,目下是天价,高攀不起,野生黄鱼焖土灶饭只可偶一尝之。好在我是个能拼凑的东说念主,家里烧鱼,盘底鱼汁和碎鱼肉用来拌米饭,相通鲜甜落胃,也算是低配版的海鲜饭。
鲨油饭最是生猛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东海海域有多样鲨鱼,当地渔民组织捕鲨队,出海渔猎鲨鱼,成绩颇丰。捕到姥鲨后,取下两片魁梧的鱼肝,切成小块,熬出鱼油,再倒入猪肉、豌豆粒、萝卜丁、香干丁,浸泡过的粳米如同好好先生,安抚着多样食材,让它们能鲜鲜与共,各鲜其鲜。一番挥铲翻炒,鲜味地覆天翻而来。吃完,油嘴一抹,鲜味在唇边三日不散。
三
从前住在前丁街,一出小区门,左手边即是姑嫂开的海味小餐馆,一到冬天,带鱼饭、砂锅海鲜面、砂锅海鲜粥的鲜味混着白气飘外出,勾得东说念主挪不动脚。我最爱她们家的海鲜粥,锅里有虾仁、海参、鱿鱼、蛤蜊,再撒点碧绿芹菜碎,险些即是竹苞松茂,咸鲜幽香,一碗下肚,周身热烘烘。我家彪兄是山里东说念主,嫌海鲜粥腥臊吞吐,我却从中尝出波澜彭湃的鲜味。
在浙东,到了立夏、白露这些骨气,海鲜饭成了时令饭。立夏饭,敝乡称醉夏饭,山里多用豌豆、笋丁、蚕豆这些时令鲜蔬和糯米同煮。海边则以海鲜咸饭迎夏,烧饭时加上鲞丁、虾仁干、咸肉、蚕豆,一揭盖,鲜香扑鼻。
除了海鲜作念成的海鲜饭,还有淡水鱼虾作念的鱼饭。一千年前,宋仁宗与臣子张景拉家常,问他老家有啥可口的,张景答:“新粟米煮鱼子饭,嫩冬瓜煮鳖裙羹。”鱼子饭是畴昔新米煮带籽淡水鱼作念成的鱼饭;鳖裙,即团鱼背壳上的裙边,与嫩冬瓜同煮,味鲜无比。
鲁迅在南京路矿学堂修业时,尝过鲈鱼饭,因为味好意思,他还成心记下一笔:“生鲈鱼与新粳米炊熟,鱼须砍小方块,去骨,加秋油,谓之鲈鱼饭。味甚鲜好意思,名极雅饬,可入林洪《山家清供》。”我着实念念不出鲈鱼饭有啥可口的。
苏州有三虾饭,以虾脑酱、虾仁、虾子与米饭同炒,细腻是细腻的嘞!说到苏州东说念主的细腻,怎样也得提一嘴那儿的银芽塞肉,不外是无为的芽菜炒火腿丝,却要用针把芽菜挑空,再塞火腿肉进去,比在蚊子腿上割肉还要细腻。
钱王梓里的台州,在吃喝上向来利弊;吴王梓里的苏州,饮食细腻如拈花。两地饮食,一个如铁马秋风,一个似杏花春雨。